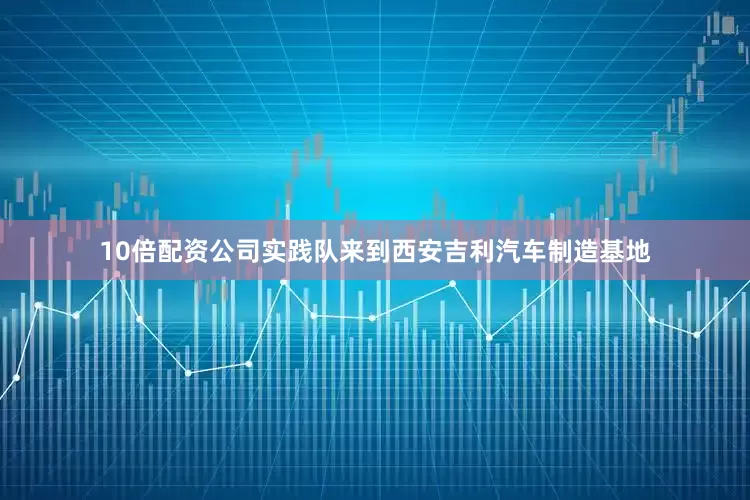1
网上流行一种说法。倘若李隆基早逝十年,必位列中国历代圣君之前五。
此说法有一定理,但观之不妥。李隆基即便英年早逝,亦仅能保有其个人声誉与历史地位不受损。然而,唐朝所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以及他本人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,并非其过早离世所能轻易化解。
安史之乱的爆发,以及唐朝由盛转衰的轨迹,实则与李隆基的政治修为、热衷于宏图伟业,以及所背负的历史重担密不可分。
而这些负面问题,在后世被誉为“开元盛世”的辉煌时期,便已显露无遗。
2
身为皇子,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取代李渊,登基成为唐朝的皇帝,主要凭借的是其卓越的军事战功与卓越的政治手腕。然而,即便如此——在登基为帝之前,李隆基并未显露其正面领导才能,反而在那股革故鼎新的历史洪流中,频繁运用阴谋与政变等手段,这才使他成为了皇位上最有力的角逐者。
公元690年九月,皇太后武则天登基称帝,将国号由唐改为周,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帝。她同时册封武承嗣为魏王,武三思为梁王,从而奠定了武周王朝的根基。
历经六年傀儡帝位之困,唐睿宗李旦终遭贬,沦为皇嗣。(让位兄长李显)、相王,李隆基等皇子们不幸被软禁于宫中,长达近十年之久,不得外出。
那一年,李隆基尚且稚嫩,年仅五岁,便被迫步入了一段终日惶恐不安、与世隔绝的幽闭生涯。
武则天得以执掌朝政,其根本缘由在于唐高宗李治晚年体弱多病,她在代理皇权的过程中,成功培植了亲信,树立了威望。实际上,武则天成为皇帝,亦是作为李氏之媳、皇帝之母的身份,再度行使皇权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,武周王朝的根基本就摇摇欲坠,其兴衰成败几乎全然取决于武则天一人的命运。一旦武则天显露动摇之态,那些誓守唐朝忠心的臣子们,定然不会放过这唾手可得的辅佐圣主之机。
705年正月,武则天病危。
把握良机,宰相张柬之、天官侍郎兼同平章事崔玄暐、司刑少卿桓彦范、相王府司马袁恕己、相王府长史兼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崇、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等官员随即联手,发动了一场政变。相王李旦凭借武则天所赐予的“知左右羽林卫大将军事”这一职位,率军驻防洛阳周边,巩固政变盟友的防线,并时刻待命,随时准备提供支援。
随后,武则天退归幕后,皇嗣李显顺利登基,复辟大唐王朝。在此过程中,相王李旦晋升为安国相王,太平公主亦晋封为镇国太平公主。与此同时,众多功臣亦获得了郡王、国公、郡公、宰相、大将军等显赫官职,使得众人皆大欢喜。
政变之后,李隆基因相王李旦的助力,由昔日备受冷落的皇族成员,一跃成为权势显赫的亲王之子。
这是李隆基命运的关键转折。
然而,李隆基的运势远不止于此,历史的大潮正一步步将他推向舞台的中央。
武则天执掌朝政数十年,其间她培育了众多心腹和党羽。即便她退居幕后,武氏势力并未随之消散。这些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,必然会对曾经的权力格局进行反扑。与此同时,皇帝李显的势力基础单薄,而相王李旦与太平公主的地位显赫,权力分散,使得唐朝的政权运作变得复杂,大臣们亦难以凝聚共识。
若无核心人物坐镇且各方利益悬殊的朝堂,纷争必将频现,直至最终决出唯一胜者。
武则天退位后,唐朝大乱。
公元706年,张柬之与众位臣子联名奏请李显除掉武氏一族的重臣。然而,武三思此人身前曾是李显的太子宾客,二人间交情颇深。李显意图构建一个由李氏宗室、武氏亲贵以及复唐功臣三者紧密联合的政治架构,因而果断地拒绝了张柬之等人的诉求。
继之,武三思凭借上官婉儿、韦皇后的助力,以及安乐公主的联姻,促成李显将张柬之等官员贬谪,从而军政大权悉数落入武三思之手。
复唐功臣,败。
在公元707年,太子李重俊因无法容忍武三思的欺凌,遂与李多祚共谋,将其翦除,致使武氏家族中的亲贵几乎悉数丧命。此后,李显再度召集兵马,镇压叛乱,最终导致太子李重俊命丧黄泉。
武氏亲贵,败。
公元710年,韦皇后与安乐公主心生异念,一者欲效仿武则天,执掌天下大权,另一者则怀揣成为皇太女的野心,企图登基称帝。于是,母女俩密谋在饼中下毒,意图毒害皇帝李显。随后,她们大力提拔韦氏家族成员,积极筹备,意图建立韦氏王朝。
历经数度惨烈的政权争夺之后,昔日的辉煌复唐功臣、武室宗亲,以及皇帝李显,均已相继淡出历史的聚光灯下。朝堂之上,仅存相王李旦、太平公主以及韦氏一脉三股势力。
李旦与太平公主为兄妹。
韦氏图谋篡唐。
无需多言。相王李旦与太平公主迅速结盟,共同发起了政变,一举铲除了韦氏一族,随后共同推举相王李旦登基为帝。
韦氏诸人,败。
据史料记载,相王李旦素以淡泊名利著称,对政治纷争不感兴趣。因此,本次政变乃由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策划发动,李旦对此事毫不知情。
然而,这却引出了一种难以解释的现象,即:在武则天晚年之际,李旦曾领兵介入政事,助力唐朝的江山得以稳固。此刻,韦氏一族企图效法武则天,篡夺唐朝皇位,李旦是否能够对此事坐视不理?
何况,李旦曾六载君临天下,且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唯一的在世之子。面对如此动荡的朝政,他难道就毫无复辟的念头?
常理下,这两点均不可行。
因此,我认为,那场针对韦氏家族成员的政变,实乃李旦与太平公主所策划,然而出于谨慎考虑,李旦悄然退居幕后,而李隆基则代表他联络禁军将领,身先士卒,勇往直前。若政变不幸失败,李旦仍可借“不知情”之由,庇护李氏宗室,保留家族血脉的最后一线生机。
从宏观政治格局考量,李旦的举措实为明智之举;然而,若从个体视角出发,李旦未能充分认识到“身临其境”的巨大影响力,然而,正是这场政变,使得原本缺乏政治根基的李隆基,在军界与朝廷中迅速树立起了自己的声望。
继李旦恢复帝位之后,李隆基逐步壮大其亲信势力,与太平公主并驾齐驱,共同成为唐朝朝堂上的璀璨双子。
公元712年8月,鉴于需要调和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之间的势力均衡,以及确保李隆基的皇位稳固,不被太平公主所篡夺,进而保证皇位能延续至自己这一脉,李旦遂作出退位决定,自请担任太上皇之职,而李隆基则继位为帝。
与此同时,李旦颁布了一则引人深思的法规:“三品官员以上的授职及重大刑罚的裁决,均由上皇亲自决断,其余事务则由皇帝自行处置。”
这就意味着,李旦承袭了“幕后操纵”的政治传统,牢牢把握着唐朝大政方针的最终决策权,而李隆基则主要负责处理日常政务。
不出一年,李隆基与太平公主间矛盾激化,终致冲突爆发。太平公主败北,遭李隆基赐命处死,其数十载积累的家产亦尽数充公。
鉴于政治平衡已被打破,李隆基已完全确立其一家独尊的地位,李旦自然也就丧失了继续垂帘听政的资格。因此,在太平公主离世之后,李旦颁布了一道圣旨:
“军国政刑,皆由皇帝决断。”
李隆基,至此跃升为武则天继任者之后的又一政治中枢要员,成为中唐动荡局势中的最终胜者。
3
刚刚执掌政柄的李隆基,尽显明君风范,积极推行诸多善政——
拜姚崇为相,将日常政务悉数委托其全权处理,被誉为“专任其事”。姚崇提出了包括“抑制权臣、宠爱爵赏、广纳忠言、拒绝进贡、不与群臣亲近”在内的诸多建议,李隆基无不采纳。
集结二十万雄师于骊山之麓,举行盛大演武,旨在检验军队的整体素质,并从中选拔出杰出将领。
复立右御史台,以严督地方州县之纪律,进一步巩固朝廷对各地的严密监控。
在与京畿各县县令的会面中,我阐述了“郡县治理,天下方能安宁”的至理名言,并郑重提醒他们,作为地方的父母官,务必尽职尽责,悉心培育和守护所辖地区的广大民众。
亲身拜谒都督、刺史、都护等地方军政大员,从而加深了皇帝与地方军政官员之间的密切联系。
规定“选拔具有才识的京官,除担任都督、刺史外,都督、刺史若政绩显著,亦得晋升为京官”,以此推动朝廷与地方官员间的职务交流与多岗位锻炼。
自武则天始,显贵与官员竞相修建佛寺,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。李隆基皇帝遂下诏削减全国僧尼,迫使一万二千人还俗务农。
薛王李隆基的舅舅王仙童对百姓欺凌无度,李隆基遂命姚崇严加惩处,此举迅速扭转了贵族豪戚横行不法的不良风气,“自此,权贵们无不收敛。”
回归贞观之治的“公共政治”模式,官员上奏或谏官弹劾,均需在众目睽睽之下宣读奏章,史官则需如实记载于史册。同时,严格禁止武周年间的“秘密政治”与“酷吏政治”现象。
.........
这一件件一桩桩,若单独立论,每件事皆可在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而如此众多的举措,竟在开元元年、二年之际一并推出,由此不难想象,对当时唐朝朝野造成了何等的震动。想必,所有人都认定这位君主堪称仅次于李世民的英明之主,仿佛大唐的晴空已然敞亮,盛世之光即将普照大地。
李隆基的仁政与朝野的深切期许,共同催动着唐朝迈向巅峰之路,成就了那段光耀千古的开元盛世。
4
然而,李隆基在施行仁政之际,亦因个人偏好而推行诸多弊政,对唐朝的政治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。
在贞观盛世,李世民确立了制度规范,规定内侍省不得设立三品官职,使得宦官不能与宰相享有同等地位,他们仅限于执掌宫门守卫、传递诏书等职责。然而,李隆基即位后,鉴于高力士在政变中立下的赫赫功勋,遂迫不及待地将他擢升为从三品的右监门将军,赋予他掌管内侍省的职责。
未几,皇宫之中宦官的数量攀升至三千余众,其众皆着紫袍。(三品)、绯衣(四五品)的就有千余人。
自李隆基之手开启,唐朝宦官的势力便如同脱缰之马,自此不可遏制,为后世宦官专政之风气奠定了恶劣的开端。
唐朝沿袭了北朝的风俗,对“宗王领兵”的制度尤为推崇。尽管此举可能导致宗王势力过度膨胀,然而不可否认的是,宗王始终扮演着皇权的延伸、王朝的支柱,以及平衡朝堂势力的关键角色。
唐朝宗王利大于弊。
登基为帝后,李隆基表面上对宋王李成器、申王李成义、岐王李隆范、薛王李隆业等兄弟颇为看重,实则并未赋予他们任何实质性职责。尽管他们后来被任命为刺史、都督,却只是虚领其名,日常仍以陪皇帝饮酒、跳舞、打球为乐。
继而,李隆基着手营建了十王宅与百孙院,将自家的子孙囚禁其中,严禁他们外出任职,更不容许他们与朝中大臣有所交往。
宗王领兵之制已然废止,李隆基独揽朝政,天下之权尽归其一身。自此,唐朝皇权丧失了最为倚重的辅佐。危机降临之际,再难觅得如李世民般力挽狂澜的英主。
唐朝时期,地方行政体系以州县为基本架构。李隆基认为,对数百个州进行直接管辖显得力不从心,于是萌生了在州之上增设一级行政机构的构想。这一新设的行政层级的职责,大致相当于现今的省级政府,旨在协助朝廷更好地治理各州。
原本此事并无大碍,治理模式随时代之变迁而演变,纯属自然之理。
李隆基本有能力建立起一套常规的政府管理体系以管理各州,他完全可以通过吏部的选拔程序、宰相的审核以及皇帝的最终批准,来任命新一届的政府官员。然而,他却另辟蹊径,挑选了一众节度使、采访使、按察使等特殊职务的使节。
为什么?
鉴于常规政府官员遵循着严密的行政程序与规定任期,他们无法无原则地执行李隆基的指令。相对而言,职官并非常规政府官员,他们不受繁琐规矩的束缚,因而能够无条件地遵从李隆基的号令。
说到底,李隆基意图避开朝堂与政府常规程序,另辟蹊径,将个人意志直接推行至地方。
然而,严格的行政程序与任职规定,无形中束缚了李隆基的决断力,亦制约了官员们的行为,使得他们不敢过于放肆,这对于维护唐朝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大有裨益。任职之便为李隆基敞开了一扇便捷之门,然而亦释放了官员们的束缚,赋予他们以李隆基之名义,图谋私利的契机。
安禄山等节度使之所以能在边镇称霸一方,实则是因为他们巧妙地利用了该制度的缺陷。
若上述三条政策乃李隆基个人所倡导之弊政,那么“制度崩溃”则成为他始终未能化解的唐朝深层次结构性难题。
唐朝的根基制度,源于北魏时期的均田制与府兵制。
此制度规定,朝廷需掌握庞大数量的国有土地。待青年男女成年后,朝廷将依据既定标准分配田地于他们。一旦获得土地,他们便需向朝廷缴纳赋税,并受折冲府的管辖,履行征战边疆的职责。
凭借土地的合理分配,唐朝构筑了一整套兵农相融、军政一体的制度体系。
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国家安定,唐朝人口日渐膨胀,土地兼并的现象日益严重,朝廷控制的国有土地随之逐渐减少。到了开元年间,朝廷已无力分配土地给适龄的青年男女。
既然青年男女不再觊觎土地,他们亦随之卸下了纳税、服役的重担。于是,唐朝的税源逐渐枯竭,兵员常年处于短缺状态。
面对此等困境,李隆基深思熟虑,提出了两种应对之策。
为缓解兵员短缺的困境,李隆基毅然决然摒弃了府兵制,转而采纳了募兵制。短短一个月内,便成功招募了十三万精壮丁勇,其效率远胜于府兵制。
症结在于,府兵制实行兵农合一,朝廷仅需提供一片土地即可养兵,成本极为低廉。然而,一旦改为募兵制,朝廷需承担发放军饷、制作装备以及奖励功勋等费用,养兵成本将增至原来的四五倍以上。
这项改动加剧了财政困境。
面对日益加剧的财政困境,李隆基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增加税收以及广泛搜刮民间财富。
在公元718年,亦即唐玄宗开元六年,为了妥善解决州县官员的薪俸难题,皇帝李隆基采纳了秘书少监崔沔的建言,下令在民众常规赋税之外,额外征收部分税金,专用于支付州县官员的薪资。
征收额外税费之举,非一而再,即再而三。一旦启动,便难以逆转,唯有零次或无数次之别。
公元721年(开元九年)李隆基再下旨命监察御史宇文融对州县的人口与土地进行全面清查。若能于账册之外额外发掘人口与土地资源,朝廷便得以拓展新的税源,开辟新的财路。
宇文融为了达成财政目标,州县官员亦竞相追求政绩,因而大力搜查人口与土地。若确无实数可供上报,他们便虚构数据,予以登记造册。
在这种背景下,唐朝的账面数据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态势。
“全国户籍人口增至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户,总人口则攀升至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人。”
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,唐朝的人口与户数激增至171万户,总人口达到了829万,同时,土地面积也实现了同步的增长。“田亦称是。”
无论数据是否属实,宇文融已然将其上报,州县据此向朝廷缴纳赋税。若未能达标,便被视为不称职,轻则遭罢黜,重则可能被流放并抄没家产。
结局显然是州县官员对民财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搜刮,使得民间哀声遍野,怨声载道。
在李隆基的统治时期,唐朝逐渐深陷于一场恶性循环之中,这一循环始于土地制度的崩溃,进而导致财政和兵员的枯竭。为了应对这一困境,朝廷不得不转向募兵,但这进一步加剧了财政的恶化。为了弥补财政赤字,政府不得不增加税收,这又引发了州县的动荡。随着人口逃亡和土地荒芜,财政和兵员状况持续恶化,形成了一个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。
国事纷繁,若是李隆基能效仿汉文帝的节俭风范,自是无可厚非。然而,他性格活跃,难以闲居,要么耗费巨资举办盛大的宴会,要么派遣精锐之师开拓疆域。
ICU还吃砒霜,能好吗?
总而言之,在结构性矛盾与李隆基的昏庸统治的双重作用下,唐朝早已外强中干,金玉其表,败絮其中。世人所津津乐道的开元盛世,实则已是千疮百孔,腐朽不堪。
5
对李隆基在“开元”年间所行举措进行简要回顾,我们便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——
李隆基的诸多善政虽看似光鲜亮丽,起到了矫正混乱的作用,却未能触及到唐朝深层结构性矛盾的根本。此类措施与儒家所倡导的,仅限于表面的、不触及实质的“改良”并无二致。
李隆基的诸多弊政,不仅严重破坏了唐朝的政治生态环境,更加剧了唐朝内在的结构性矛盾。
在这此消彼长的演变中,唐朝的国运在经历了短暂的“开元盛世”之后,便急剧下滑,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全方位的创伤。
从这一视角审视,所谓开元盛世实则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般完美无瑕,它更像是在北魏以来悠久历史的长河中,历经巅峰后的必然产物。而随之而来的安史之乱,宛如为北魏以来历代英雄豪杰奏响的一曲凄美而壮烈的告别之歌。
李隆基固然具备明君的风范,然而细观其所作所为,其个人能力与苻坚、杨广等历史人物相去未远。
李隆基之所以能够占据今日的历史高位,实乃时运使然。
配资平台网址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10倍配资公司实践队来到西安吉利汽车制造基地
- 下一篇:没有了